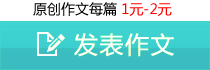喪鐘為誰(shuí)而鳴?
千年前,柏拉圖于《理想國(guó)》中描繪了一群終日囿于洞穴之內(nèi)的“影子人”:他們只能通過(guò)墻壁上的影子感知外面的世界,情感在經(jīng)年累月的囚禁中早已殆盡,失去了價(jià)值觀和人性。千年后的我們,身處于后工業(yè)時(shí)代計(jì)算機(jī)浪潮之下,也應(yīng)警惕,在與計(jì)算機(jī)日語(yǔ)趨同的思考中,逐漸失去價(jià)值觀和同情心的可能后果!
當(dāng)我們的思想被機(jī)械化,價(jià)值觀、情感等人性的部分被逐漸抽離,我們將淪為易于操縱的木偶。簡(jiǎn)單的思想,便可將我們玩弄于鼓掌中。而當(dāng)這種思想變得極端,社會(huì)便會(huì)被拖下暴虐的深淵。喬治·奧威爾在《1984》中展現(xiàn)了一個(gè)所有的言論都被操縱,人們的思想在機(jī)械化的生活下日益趨同和沙化的恐怖社會(huì)。如此社會(huì)中,幾乎每一個(gè)人都只能機(jī)械地思考,情感、活力、溫情和基本的價(jià)值觀等人性的屬性在思想警察的監(jiān)督下全部被扼殺。這樣的集體絕非涂爾干所言的“有機(jī)團(tuán)結(jié)”,不過(guò)是失去了人性的機(jī)械化的人類的集合。是故,于計(jì)算機(jī)浪潮中,我們必須時(shí)刻注意,不讓我們的思考變成計(jì)算機(jī)思考的方式,不令書中的悲劇重演。我們都畏懼一個(gè)“戰(zhàn)爭(zhēng)即和平,自由即奴役,無(wú)知即力量”的集權(quán)統(tǒng)治社會(huì),認(rèn)為自己不會(huì)成為其中的一員。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們,除溫斯特外,最初也從未意識(shí)到自己早已身處巨大的洞穴,在日復(fù)一日中被影子化和符號(hào)化。
必要的警醒在當(dāng)下后工業(yè)化社會(huì)中不可或缺,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否定計(jì)算機(jī)浪潮下回歸的理性思考。我們否定的不是光的波粒二象性抑或引力波中的哲思,也非康德《純粹理性批判》與《實(shí)踐理性批判》中的理性。我們否定的,是人像計(jì)算機(jī)一樣思考后,失去的人性的光芒。當(dāng)個(gè)體被剝離了價(jià)值觀和同情心,試問又如何創(chuàng)造出溫克爾曼筆下的“高貴而單純、靜穆的古希臘文學(xué)”?千年前的古希臘和古羅馬沒有計(jì)算機(jī),沒有如今便利的生活,但也沒有像計(jì)算機(jī)一樣思考的個(gè)體,于是,維吉爾、阿那克利翁、薩福和品達(dá)羅斯魚貫而出,古文學(xué)的天空星光燦爛。計(jì)算機(jī)式的思考扼殺了我們的創(chuàng)造力,我們的情感只能在膚淺化的道路上逐漸式微。因此,拒絕像計(jì)算機(jī)一樣思考,不是對(duì)理性光芒的否定,而是一種愛與情感的回歸,一種情感和價(jià)值的回歸。正如金斯堡于《嚎叫》中所言:“我仍深愛自己和全人類。”呼喚情感式的思考,避免計(jì)算機(jī)式的思考,是對(duì)于自我和他人人性、人情的尊重。我們珍惜自我心靈中人性的微光,因而對(duì)像計(jì)算機(jī)一樣思考抱有謹(jǐn)慎而清醒的態(tài)度,這種人性是人與蕓蕓眾生相區(qū)別的重要特征。有溫度的思考才是人的行為。
黑塞出生于工業(yè)化浪潮席卷的時(shí)期。自伯爾尼來(lái)到風(fēng)光秀美的堤契諾后,他曾前往阿爾卑斯山南麓的圣教堂。圣母依舊,但卻也已受到工業(yè)化的影響,于是作為一個(gè)古文明崇尚者,他終于無(wú)不悲哀地意識(shí)到,農(nóng)業(yè)文明終將落幕,金錢將戰(zhàn)勝道德,機(jī)器將戰(zhàn)勝田園之樂。但他厭惡的不是機(jī)器,而是心靈的淺薄和思想的冷漠,缺乏人性。此言如黃鐘大呂,不僅為彼時(shí)的人們敲醒了警鐘,更令我們?cè)诋?dāng)下計(jì)算機(jī)潮流的大勢(shì)所趨中清醒地明白:我們不反對(duì)理性,我們應(yīng)警惕的是思想被計(jì)算機(jī)的同質(zhì)化和價(jià)值觀、同情心等人性部分的式微。如此,我們便可信步走入寂然、晴空,感知世界的美好。
切莫讓自我的思想,人性的光芒消亡。切莫令喪鐘為我們的思想而鳴!
本文地址:喪鐘為誰(shuí)而鳴?https://www.www.kovpower.com/a/8440.html